李海鹏 | 推荐书评《去德黑兰》:漫天打杀声中的犀利解构和大胆建言
时间:2021-12-31 作者:
美国与伊朗关系是决定当前中东地区权力平衡以及诸多热点问题走势的重要因素。
由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现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弗林特·莱弗瑞特与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高级讲师希拉里·曼·莱弗瑞特合著的《去德黑兰:为什么美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解》(以下简称《去德黑兰》)于2013年由纽约大都会书局出版之际,旋即以其关于美伊关系和伊朗内政外交的“另类”观点,在美国中东学界和政策届引发激烈争论。该书中文版的引介,可为国内关注伊核问题、美伊关系和中东局势的学者以及各界读者提供了别样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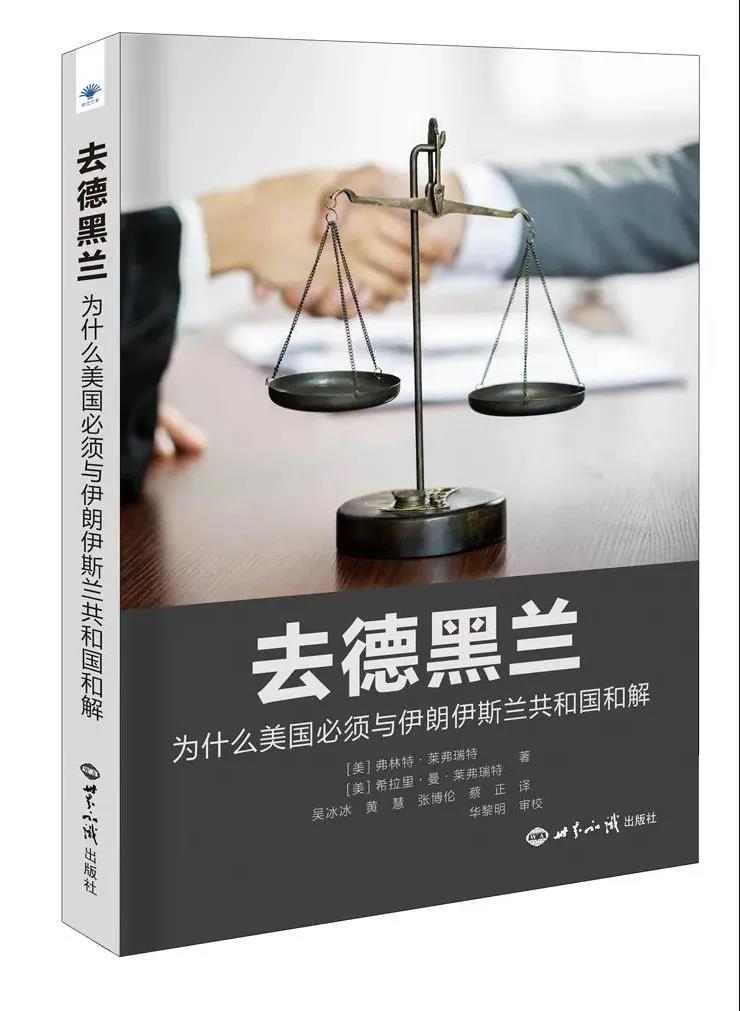
《去德黑兰》一书认为,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政府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国内政治的评估以及美国的应对方案就存在严重误判,进而将三大“迷思”(非理性、不合法、孤立)作为美国对伊政策的基础,这些政策恰恰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全书分三个部分逐一批驳了上述迷思。作者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是复杂历史遗产和战略认知的产物,是高度理性的,体现为冷战后历届伊朗政府为缓和美伊关系多次与美国主动接触的尝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秩序具有历史、意识形态、制度、绩效等多层次的内生合法性,而西方对伊朗2009年总统选举的舞弊指责和对“绿色运动”的支持,恰恰反映出部分西方人对伊朗政治现实的扭曲认知和价值偏见。美国对伊的孤立政策并未加速伊朗崩溃或催生一个亲美、亲民主的伊朗政府,而孤立政策(以及“不理性”、“不合法”迷思)本质上是美国霸权利益与政府内外“伊朗迷思”制造者和支持者相互支撑的产物。最后,作者呼吁美国决策者基于国家利益,在对伊政策方面创造另一个“尼克松时刻”,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达成全面和解。
不难发现,本书是两位有着丰富外交工作经历的美国学者关于美伊关系的深刻政策评估与建言之作。其独特的视角和观点对于国内伊朗国别研究、中东区域研究以及相关政策部门,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参考价值。
第一
从美国对伊政策制订参与者、执行者的视角对美伊关系史的全景式回顾。
《去德黑兰》一书的两位作者曾长期在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任职,亲历或参与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制定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大量内部讨论,也因而有机会接触到伊朗政府相关机构的高层官员。
据笔者粗略统计,全书中至少10处以上细节是基于作者在美国政府任职期间的所历所闻,此外还有多处属于作者在离开美国政府部门后与伊朗高层官员接触中所获得信息。作者细致梳理了拉夫桑贾尼、哈塔米时期伊朗政府对美国的六次缓和尝试以及美国政府的消极回应,勾勒出美伊关系历史发展的迂回曲折的同时,也反衬出伊朗决策者的现实理性以及伊朗“迷思”在美国政策届的强大影响。其中基于内部视角的丰富细节,无疑为国内学界理解美伊关系发展史提供了深刻洞见。
第二
基于伊朗本土视角和材料对美国国内关于伊朗“迷思”的解构。
作者强调自己是设身处地并客观地记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身在世界的位置、如何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以及(如何)在伊朗人民中建构合法性”,最终目的是解构美国政策届普遍存在的关于伊朗政府之性质(“不合法”)与行为(“不理性”)的迷思,其基于的主要材料包括大量伊朗官方材料、国内研究以及作者与伊朗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广泛交流等。当前我国学界关于伊朗和中东国家内政外交的研究往往深受西方学界和政策届产品的影响,相对缺乏基于本土资料和调研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其信息来源的局限性如何,《去德黑兰》一书无疑可丰富国内学界对伊朗内政外交的理解。
第三
从思想派别、利益集团、思想库的角度透视美国对伊郎外交决策的影响因素。
作为一部解构之作,《去德黑兰》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深度揭示美国国内关于伊朗的迷思与现实、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巨大反差,也在于其对相关迷思的制造者/支持者及其与美国霸权利益之间相互塑造关系的犀利剖析和批判。
作者指出,美国“政府内外充满偏见的精英们”(包括新保守主义者、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以色列院外集团、伊朗海外侨民),共同“炮制”了美国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性质(不合法)、行为(非理性)以及美国解决方案(孤立)的三重迷思,其根本出发点是服务于美国的帝国战略,即在中东地区“强化一个亲美的地区秩序”。更宝贵的是,作者以惊人的勇气深度披露了大量参与或影响美国对伊朗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外交政策制定的党内集团、人物、智库和利益集团。
当然,美国对伊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众多集团博弈的复杂政治进程,涉及总统和其他行政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会、利益集团、思想库、媒体和公共舆论、学界等广泛因素。《去德黑兰》一书显然无法反映美国对伊朗外交决策的全貌,但其具名直录的做法显然有助于从某些侧面深化国内关于美国对伊外交决策过程的经验和理论认识。
第四
解构后的大胆建言,呈现美、伊决策部门内部的多元声音。
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40年来,美国总统换了八届,无一例外都实行敌视伊朗的政策”。但《去德黑兰》一书同样反映出美国政策界在对伊政策上存在多种声音,其中至少有一支声音呼吁全面缓和美伊关系、减小在中东地区战略投入、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在伊朗国内亦不乏支持与美国和解的力量。2015年伊核协议签订至今美伊关系所经历的反复,恰恰印证了两国政策届不同观点、政策派别的存在和激烈交锋。“和解派”在美、伊两国政策届的规模、影响力如何?仅依据《去德黑兰》一书尚难得出确切的评估。但该书所凸显的特定政策取向,却是我国相关部门在制定对伊朗、中东地区政策乃至地缘战略时不容忽视的变量。
不难想见,这样一部观点尖锐、文笔犀利的解构和建言之作,出版后即在美国学界和政策届引发激烈争论。
在笔者看来,关于《去德黑兰》的诸多批评声音中有一点颇值得玩味。部分批评者认为,该书论证中存在逻辑不一致之处,即作者在对美国对伊政策的解构批评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立场,与其对伊朗政权合法性的解读甚至“辩护”相互矛盾,因为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如果在对伊朗政策方面一种‘尼克松式的’转型能够扭转美国权力和地位的相对下滑,那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否是个合法政权就不再重要了。”笔者看来,上述批评恰恰是对作者现实主义战略思维的一种误读。作者开篇即开宗明义指出“明智的战略计算的根本......是‘互动决策’”,而互动决策的有效性则有赖于对竞争对手价值观、战略关切、认知和目标的准确把握。
任何学者在研究中都无法完全避免对其研究对象的主观价值评判,《去德黑兰》一书的作者也不例外,但该书作者的初衷却是“设身处地并且客观”地呈现伊朗官方和多数人的理念和认知,以便为美国决策者对伊互动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说本书所解构的伊朗“迷思”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现实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考虑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矛盾交织,《去德黑兰》恰如一剂解毒剂,警视美国决策者在外交决策中需理解、反思乃至尊重他国基于自身历史经验而形成的理想信念和道路选择。
作者:李海鹏
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



